
1938年1月,梁漱溟(左)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交谈时的合影。(出版社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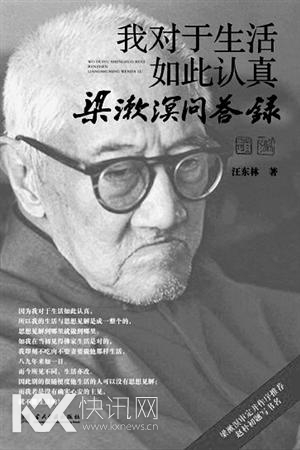
《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9月定价:36.00元


▲20世纪80年代中期,梁漱溟(左)与《梁漱溟问答录》作者汪东林合影。 (出版社供图)
10月18日是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诞辰120周年,这位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学者,拥有让后人享用不尽的思想成就。记者从当代中国出版社获悉,唯一一部经其本人审定的传记《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在绝版多年后终于修订再版。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策划编辑李丽铮介绍,该书首次出版于25年前,作者在特殊年代里记录、整理了梁漱溟在“文革”中的各次发言以及受批判斗争的情况,独家披露了包括1953年梁漱溟与 毛泽东 之争、“文革”中拒绝“批林批孔”等重大历史内容在内的1949年以后梁漱溟39年人生轨迹,为海内外梁漱溟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档案材料。
诸多史料首次面世
梁漱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不仅因为他是“五四”运动之后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他还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然而,在1953年9月,梁漱溟却因国事大胆谏言,遭到“以笔杀人”的“杀人犯”、“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伪君子’”等斥责和辱骂,并从此戴上一顶“反面教员”的铁帽子,被“冷藏”了几十年,直至1979年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以解脱。
谈起新版书名《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李丽铮告诉记者,这句话出自梁漱溟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教书期间写下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道出了梁漱溟特立独行、表里如一的品格和思想底蕴。
该书作者汪东林多年专注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自1980年5月出版《 李宗仁 归来》至今,已撰写出版了十多本人物传记作品,其中大部分以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为传主。
“在这些著作中,就史料价值而言,排在首位的应该是《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告诉记者,包括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争、“文革”中拒绝“批林批孔”等重大历史内容在内的1949年以后的梁漱溟先生39年的历史轨迹,都在这本书中,首次与世人见面,且大部分都是他“亲历、亲知、亲闻”。
“冷藏”20年结下特殊友谊
“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8年6月梁漱溟先生病逝,我曾有幸长时间地与他相随相交。” 汪东林回忆说,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20年间,正是梁漱溟先生与世隔绝的被“冷藏”时期,他唯一发声的舞台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即平时学习改造的场所。“梁漱溟先生是这个学习组的成员之一,而我则是这个学习组的记录员。”汪东林告诉记者。
按照当时的规定,非特殊情况,这种每周2到3次的学习会只作内部情况反映,不作公开报道。因此梁漱溟在这20年间的一言一行,包括多次遭受批判的记录,除了简报内部反映,就剩下“记录员”汪东林的笔记本了。
在汪东林的印象中,那20年间,梁漱溟是学习组发言较多、“放毒”也最多的“明星”组员。“单是专为他开设的专题批判会就有四五次,每个专题进行几个月甚至一年,批判会的次数则难以统计。天长日久,我内心暗暗为梁漱溟先生事事处处坚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顾一切地顽强抗争而吃惊,并渐渐产生敬佩。”他越来越留意并认真记录梁漱溟各种有准备的长篇宏论和即兴而发的片言只语,每篇都整理成文,包括请梁漱溟本人过目。这些,都是他后来撰写《梁漱溟问答录》和其他著作最早积累的素材。
出版过程一波三折
回忆起这部书的出版始末,汪东林告诉记者,1980年11月,他应约为《北京晚报》撰写梁漱溟先生访问记,不料这篇题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的文章在11月9日见报之后,立即遭到当时主管部门的高层人士的批评,说:“梁漱溟这样的人对谁刚直不阿?报纸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乱弹琴!”
风波之后,汪东林把第三人称写作的梁漱溟传记,改写为一问一答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梁漱溟问答录》。尽管后来又遭受若干波折,但终于在《人物》杂志推出连载,而后于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
“没想到的是,刊物连载和全书出版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大报刊,海内外有几十家媒体发表评论或选载。首版印刷了三次,香港三联书店以繁体字出版,2004年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若干重要文章,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字数增加了一倍。”汪东林介绍说,此次再版的《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是第三个版本,对前两个版本做了不少修订,除了将梁漱溟写于1987年的初版序言补充在开篇,汪东林还专门撰写了《<梁漱溟问答录>出版前后》,交代了这部作品坎坷的写作过程,作为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注脚。
有些档案仍待解密
自1953年以来,最早从正面描写梁漱溟的文章就是汪东林发表于1980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的访问记,而最早一本从正面评述梁漱溟的书正是《梁漱溟问答录》。
但汪东林认为,关于梁漱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自梁漱溟病逝至今,海内外出版的有关梁漱溟的传记作品和研究专著已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真正对梁漱溟先生的深入研究,只能说刚刚起步。这一方面有待于后来者加大研究工作的力度,一方面还有待于对梁漱溟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若干档案材料进行解密。仅就我所经历、所接触、所知道的情况,其现存的档案材料,特别是高层档案材料,即便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至今仍没有对公众解密。”汪东林表示。
人物小传
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1917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1939年见团结抗战大局有不能贯彻始终之虞,和几个中间性小党派共同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为进一步实现此一宗旨,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为国内和平奔走于国共两大政党之间。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为怎样发挥诤友作用与毛泽东发生争论,被称为“反面教员”。他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并不赞同,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孔运动”更是明确表示反对。 梁漱溟自青年时代起相信人类未来必归于社会主义,人类将从中国文化汲取营养。17岁时认定唯佛家的宇宙观最正确,十年后领悟儒家精神最适合于社会大众,遂以“不住涅槃,不舍众生”对自己,而以传播儒学为毕生职志。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乡村建设理论》(1956)、《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0)等,有《梁漱溟全集》八卷存世。 (资料图片)
《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书摘
“舍弃理想,便没有我”
问(汪东林):八国联军进北京,距今已有86年了,能亲自耳闻目睹这一历史事件者如今已为数极少。梁先生对这一重大事件尚能记忆否?
答(梁漱溟):当时我已8岁,还能记得一些事情。有的是当时听家里大人说的,比如,义和团杀了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当时把这根导火线说成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主要原因。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把北京城分成八个区域,一个国家管一个地区,凡德国和日本管辖的地区,中国老百姓受害最深,因为他们极力报复;又比如,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住进紫禁城,会说外国话的妓女赛金花陪住,她还骑着高头大马在东西长安街上行走,大人都骂她是“不要脸的东西”……这些都是当时亲耳所闻。还有西太后偕 光绪 皇帝逃离北京,消息震动全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在当时一般人的脑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记得这一消息传到我家中的时候,全家上下都哑然失色,不思饮食,连小孩子也得规规矩矩,不许像平时那样蹦蹦跳跳了。后来又听说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他是谈判的翻译,精通多种外国语。听大人们说,他的后台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刘、张在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后,便提出“东南自保”,以示抗衡。辜鸿铭一面参加谈判工作,一面与张、刘电报联络。我知道辜鸿铭的名字,便是在庚子年,大人们几乎天天在饭桌上谈到他。
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自经历的。当时我家居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属美国人管辖范围。相比之下,他们对中国老百姓的压迫要稍好于德、日。但整个北京城都在外国侵略者的统治下,外边风声鹤唳,老百姓终日惶惶,都不敢轻易外出。我家也大门紧闭,足不出户。因为年纪小,这种坐牢般的日子,印象极深。有一天,忽然大门被敲得嘭嘭直响,进来几个外国兵,还有一位中国翻译。他们气势汹汹地在家里搜了一通,没有查出什么,偏偏在我的房间里,砸坏了我的儿童玩具枪和剑,使我十分伤心。然后盘问我的父亲,像查户口似的,最后命令:“不许外人留宿,违者受罚。”走到大门口,又指着大门两侧的脏土杂物厉声厉色地说:“这里太脏了,你们要天天清扫。”说完扬长而去,全家这才松了口气。父亲回到屋里一屁股坐进太师椅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问(汪东林):自抗战爆发之后,梁先生即以无党派人士和民盟负责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事奔忙。梁先生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和行动,还有什么补充?
答(梁漱溟):我从抗战初期起,即为团结抗敌而奔走于各方,抗战胜利后又为争取和平建国而代表第三方面的民盟参与国共两党和谈,总计前后有八九年之久。有人曾经在气头上说我梁某人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这当然不合事实。一个人的政治言论和行动,一旦成为事实,便涂抹不了,今人和后世自有公正的评说。诚然,在我的一生中,做不成的事,没做通的事,做错的事,都不少。即从抗战至国共两党和谈及破裂这一段历史看,亦是如此。
现在回顾,我静心反省,自己不贪安逸,不图享受,自19岁起粗衣素食,并无私产,教书著述所得亦几乎全用之于兴办教育,接济若干志同道合而经济拮据之友人。至敌寇入侵,为救国难而奔走四方,甚至自愿深入敌后,跟着抗日游击队昼行夜宿于荒山野岭之中,颇有些不怕苦、不怕死的样子。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自己呢?扪心自问,则源于自幼立志要改造中国,为国家民族做事,并确有自己为国家民族设置之理想。简言之,自己深怀爱国之情,对祖国的责任感远远超过自己的小家小我,有时甚至无我。举例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亦自有一套。这距离不易泯没,但根本上却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我对民族前途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舍弃理想,便没有我。而共产党人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即最高利益)的集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为这个远大理想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虽然远大理想的内涵距离很大,但都抱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之心,却是相通的。正是这,决定了我与共产党人合作之可能。于彼此见解主张之不同,我以为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确有同可求。多少年来,共产党人是赞同我持此见解,并把我作为一共产党外之朋友的。远如李大钊先生与我相知相交,至我建国前两次赴延安与毛泽东等先生之交往;近如建国初期毛泽东曾一度与我相交,把我和章士钊先生一同作为中南海他家中的座上客,以至毛故去之后,中国共产党自身结束了十年“文革”的大动乱,走上了复兴之路,我又成为共产党人的一位朋友。众所周知,我曾经被排除在朋友行列之外,那就是自毛泽东先生本人1953年发动的对我的批判开始,我长时期成为一名不戴帽子的“反面教员”,一有言论,甚至是零星杂感,片言只语,亦成为众矢之“的”,动不动便对我进行有组织的批判。对于1953年因我自己的荒唐而闯下的大祸,以及这以后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我的言论和遭遇,当留待以后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慢慢儿细说。
但是,就我个人而论,不论是解放前如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还是解放后我在各个时期的一言一行,其对也,其错也,都与我最早形成的理论主张和行为准则密切相关。
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中国社会的出路何在?远在20世纪20年代初,我即认识应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而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则必须先有全国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之建立,以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以上两点,我同中共的主张和愿望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在如何实现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即建立统一政权问题上,这正是1938年初我赴延安与毛泽东通宵达旦争辩问题的焦点所在。
中国前途如何,怎样统一?我潜心研究中国几千年之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对当前的社会结构和状况也进行过调查摸索,提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融伦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政治、治安于一体,以乡村为基地,从普及民众教育入手,先搞实验,一个县,一个省,逐步扩大,而避免武力,结束内战。结果呢,我的设想蓝图当然落空了。1949年由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掌握了武装,以武力统一了中国。(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快讯网立场。)



